有些遇见,注定不朽。
落到纸笔上,是18岁的王希孟,遇见《千里江山图》;
24岁的毕加索,遇见《拿着烟斗的男孩》;
37岁的穆夏,遇见《茶花女》。
年近不惑的穆夏,遇见小仲马献给法兰西的现实主义戏剧开山之作《茶花女》,一举成就了个人审美和艺术成就的最高峰。
注定与新艺术运动一道,定格于流光之上的《茶花女》戏剧海报诞生。
这,大抵就是命运。

△茶花女电影剧照
序章:遇见伟大
太阳底下无新事,《茶花女》的故事也并不稀奇。
穿梭于巴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玛格丽特,身陷泥淖、心系明月,撞上贵族青年阿尔芒用真诚和同情编织的情网,一发而不可收。
两人爱得痴缠,却对抗不了全世界:阿尔芒的父亲无法接受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,结局一开始就注定了。分手后肺病加重的玛格丽特凄凉离世,阿尔芒悔恨莫及。

△茶花女电影剧照
站在上帝视角的我们,回看遇见《茶花女》的穆夏,端的是“鲜花着锦,烈火烹油”。
可若在宏大的历史一隅凝望时间,你会发现初试锋芒的艺术家,撞上久负盛名的皇皇巨著,多的是泥牛入海,悄无声息。
小仲马把美好撕碎给我们看,说着“艺术是为了颂扬美”的穆夏,决定以直击人心的美,联结真实和虚幻,祭奠玛格丽特“既没有贞洁做基础,也没有宗教可依靠,也没有家庭可以当做归宿” 的爱情。
主旨:少即是多
给人以强烈视觉冲击的等身高画幅;莎拉·伯恩哈特迷人的侧颜;画布间满溢的灵性美。
依然是那个圣诞前夜,甫一出手便惊艳了整个巴黎的艺术家。
在这之外,为贴合人物而作的百般努力,更值得称道。

《茶花女》戏剧海报中,由来擅长给美丽做加法的穆夏,转身拐入一条写着“Less is more”的疏落小径。
抛去明丽的色彩,辉丽的装饰,唯余新雅简素的画风。
恰似风裁日染的山茶一株,不争春,不夺色,静立山间。虽姿态清淡而疏离,却轻易就烙在心上,再无法抹去。
高潮:画卷中重生
历史无数次证明:灵魂不因肉体而卑贱。
一如美丽纤细的玛格丽特,以飞蛾扑火的姿态,奔向毕生信仰“爱情”,不问归期,不计得失。纵使身躯孱弱,却难掩灵魂的高贵。
落在穆夏的画卷之上,便有了佳人凭栏,绝世而独立的一幕。这一刻,绘画与文学,小仲马与穆夏是互通的,书卷上的茶花女幻作画笔下的玛格丽特,实现了一场盛大的复活。

画面中间,不施粉黛的女子侧身而立,眼横秋水、眉如春山。
比那惊心动魄的美更引人注意的,是女子脸上拂不去的轻愁。如一束清凉的月光,打在半开的窗棂上,但觉秋意更浓。
一袭素色衣袍裹身的玛格丽特,右手扶栏,左手抓襟,弱柳扶风的诗意美,跃然纸上。
女子身上,透出删繁就简之美,一席流动的白色长袍,鬓边斜插一朵洁白的山茶,已胜过不知多少华服美冠。
单纯的美之外,素色衣饰另有一番深意:借物喻人。暗合玛格丽特的忠贞、纯洁,心性如雪色,不染尘埃。
尾声:去往星辰之上
世间好物不坚牢,彩云易散琉璃脆。
如新月,似春水般美好的茶花女,注定不属于人间,她的归途在星辰之上。

穆夏将她置于万千星辉间,夜幕之上,浅银色的群星携着大片素色,自天际而来,似近,还远。
清寒的星夜仿若四起的流言、淡漠的人心,玛格丽特无从躲藏,也无力躲藏。夜色渐浓,她也终将踏上走向星辰的路。
许是觉得夜凉如水仍不足以书写玛格丽特的人生悲剧,艺术家加入了双重意象:画面上方两侧被荆棘和树根穿透的心脏、脚边代表宿命的死亡之手,为她奏响一曲生命的挽歌。
而死亡之手擎着的那株山茶花,也不过是死神最后的怜悯,落在玛格丽特坟前的一声叹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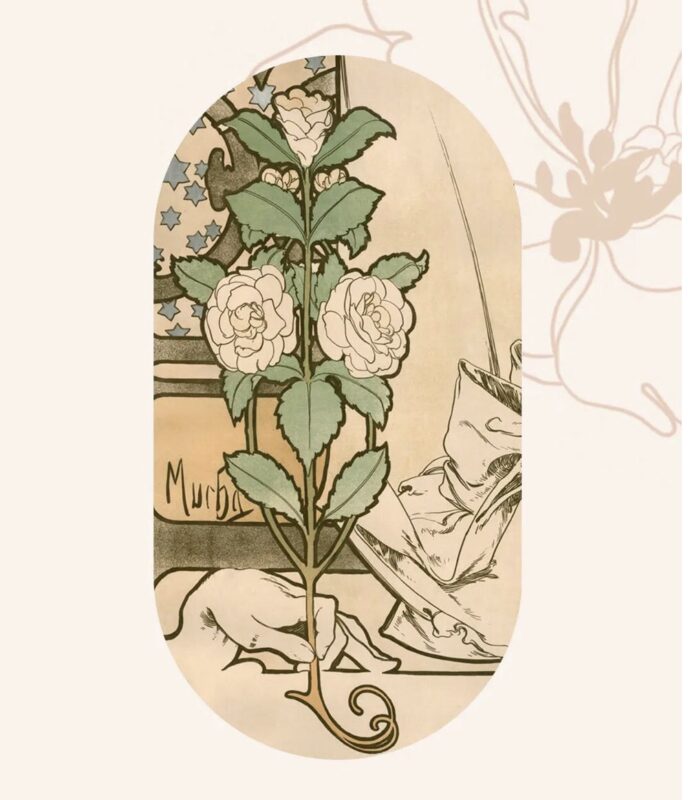
镂金错彩的美好年代,《茶花女》的初发芙蓉之美,好似春日的第一滴雨打在湖面上,温柔缱绻,让人驻足、流连。
那抹素色剪影,宛如山涧清泉、疏桐流响,见之忘俗。